寓理于事的文言文(螳螂捕蝉文言文翻译(《说苑》))
1.螳螂捕蝉文言文翻译(《说苑》)
吴王要进攻楚国,向左右大臣警告道:“如有人敢于进谏,就叫他死!”有一位舍人名叫少孺子,想谏又不敢,他就怀揣弹弓到后花园去,露水洒湿了衣裳,这样过了三个清晨。
吴王知道后说:“你来,何苦把衣裳淋湿成这个样子?”少孺子回答道:“园子里有树,树上有蝉,蝉在高高的树枝上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就在它的身后。螳螂俯着身子向前爬去要捉蝉,而不知黄雀在它身傍。
黄雀伸着头颈要啄螳螂,而不知在它的下面有我手中张开的弹丸。这三者都想得到自己的好处,而不顾身后隐藏着祸患啊!”吴王说:“您说得好啊!”于是停止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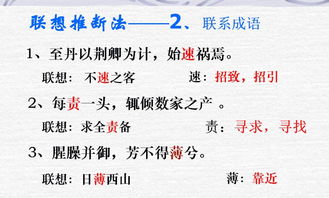
2.怎样理解《伤仲永》寓理于事的写法
赏析一:名作见精巧,临川先生的《伤仲永》思辨超人,随笔挥洒,凭一篇别致小文,引发人们不倦地探讨,不断地截获可圈可点的阅读知觉―― 立意上,寓理于事。
通过方仲永5岁到20岁才能发展变化的故事,说明了人的天资和后天成才的关系。方仲永5岁即能吟诵诗词,确有比众人聪明之处,但后天不努力,也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相反,如果一个人缺点很多,起点不高,但经过他后天的奋发图强,一心进取,还是会名留青史,可得许多人赞扬的。选材上,见闻交织。
以“闻”的形式写仲永年少时天资聪慧;以“见”的形式写仲永十二三岁才思“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以“闻”的形式写方仲永最终平庸无奇。“见”和“闻”有机结合,叙述真切可信。
剪裁上,详略有序。课文依次写了方仲永才能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详写第一个片断,铺陈方仲永才能初露的情形,突出方仲永幼年聪慧,是可塑之才,有发展潜力,暗示其前途无量,为后面写他的退化作下铺垫,突出“伤”的前提;而写其父的贪利之举导致他的才能衰退,则点明“伤”的原因。
略写后两个片断,几笔点出方仲永沦落平庸的状况,引人深思,道明了“伤”的内容。这样处理,清楚地体现了“伤”的含义,内容集中而主旨确然。
表达上,叙议结合。借一件事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阐明某种观点,叙述是基础,阐明道理是核心。
本文采用随笔的形式而写。第1、2段写方仲永的始末表现,即“为什么伤”,采用记叙的形式;第3段阐明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即“伤什么”,采用议论的方式。
作者认为人的才能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是天赋很高的人,如果不加强学习,也会变成平庸无能的人。手法上,先扬后抑。
从整个文章来看,作者显然是为仲永的经历遭遇而感伤。题目中的“伤”(哀伤、哀怜)字,就已经透露这一点。
因此叙事部分十分着意写方仲永的幼年,极言其才能何等的出众,却只是粗线条带过此后的情况,对比之下,表达出作者的惋惜之情;尔后就事说理,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画龙点睛,有力地突出了中心。 行文上,言简意赅。
一是精当传神地用词。如在第1段中,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了方仲永索求书具的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更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环谒”一出,则把仲永父贪利自得、可悲可怜的愚昧无知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是全篇的行文笔墨极省,既高度概叙,以至难以再删一字,同时也富于文采,描写细腻,与文体特点相映生辉。感悟上,天赋人为。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主要是用方仲永作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受之人”即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仲永有天才而“受于人者不至”。
天赋这样高的神童,不学习,最终也变成了普通人一样。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然的话,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办不到。
赏析二:文章开头一段,记叙了方仲永幼年聪颖的情况。先点出其“世隶耕”,出身世代为农的家庭,为下面写他的天资作铺垫。
接着,写他五岁时忽然无师自通、书诗署名的突出表现。这几句写得颇具神奇色彩。
本来“未尝识书具”——农家无笔墨纸砚,却“忽啼求之”;求得之后,不但“即书诗四句”,且“自为其名”;从此以后,又竟“指物作诗立就”。这自然被乡人视为神童了。
因为“奇”其子,连带着“稍稍宾客其父”,甚至给他钱。这本来是山乡百姓对有天资的儿童及其家庭的敬重,但竟反过来成了压抑天资的不利条件。
“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儿童的天资被无知的父亲利用来作为到处敛钱的资本,亟需在求学中发展的天资竟“不使学”。
作者对这种因没有文化和贫困带来的愚昧,在叙述中寓有讽慨;而对被利用来到处讨钱的仲永,则不无“伤”意。这几句是本段中的关键之笔。
仲永后来的结局与作者的议论,都由此伏根。“不使学”三字用笔尤重。
整段叙述,从“未尝识书具”到“指物作诗立就”到“不使学”,文意曲折多变,使读者对仲永的将来发展引起极大的兴趣。 接下来一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代了仲永从神通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
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之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代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
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
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现言外。 最后一段(教材中被省略,建议作为补充阅读材料)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

3.怎样理解《伤仲永》寓理于事的写法
赏析一:名作见精巧,临川先生的《伤仲永》思辨超人,随笔挥洒,凭一篇别致小文,引发人们不倦地探讨,不断地截获可圈可点的阅读知觉――立意上,寓理于事。
通过方仲永5岁到20岁才能发展变化的故事,说明了人的天资和后天成才的关系。方仲永5岁即能吟诵诗词,确有比众人聪明之处,但后天不努力,也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相反,如果一个人缺点很多,起点不高,但经过他后天的奋发图强,一心进取,还是会名留青史,可得许多人赞扬的。选材上,见闻交织。
以“闻”的形式写仲永年少时天资聪慧;以“见”的形式写仲永十二三岁才思“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以“闻”的形式写方仲永最终平庸无奇。“见”和“闻”有机结合,叙述真切可信。
剪裁上,详略有序。课文依次写了方仲永才能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详写第一个片断,铺陈方仲永才能初露的情形,突出方仲永幼年聪慧,是可塑之才,有发展潜力,暗示其前途无量,为后面写他的退化作下铺垫,突出“伤”的前提;而写其父的贪利之举导致他的才能衰退,则点明“伤”的原因。
略写后两个片断,几笔点出方仲永沦落平庸的状况,引人深思,道明了“伤”的内容。这样处理,清楚地体现了“伤”的含义,内容集中而主旨确然。
表达上,叙议结合。借一件事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阐明某种观点,叙述是基础,阐明道理是核心。
本文采用随笔的形式而写。第1、2段写方仲永的始末表现,即“为什么伤”,采用记叙的形式;第3段阐明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即“伤什么”,采用议论的方式。
作者认为人的才能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是天赋很高的人,如果不加强学习,也会变成平庸无能的人。手法上,先扬后抑。
从整个文章来看,作者显然是为仲永的经历遭遇而感伤。题目中的“伤”(哀伤、哀怜)字,就已经透露这一点。
因此叙事部分十分着意写方仲永的幼年,极言其才能何等的出众,却只是粗线条带过此后的情况,对比之下,表达出作者的惋惜之情;尔后就事说理,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画龙点睛,有力地突出了中心。 行文上,言简意赅。
一是精当传神地用词。如在第1段中,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了方仲永索求书具的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更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环谒”一出,则把仲永父贪利自得、可悲可怜的愚昧无知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是全篇的行文笔墨极省,既高度概叙,以至难以再删一字,同时也富于文采,描写细腻,与文体特点相映生辉。感悟上,天赋人为。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主要是用方仲永作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受之人”即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仲永有天才而“受于人者不至”。
天赋这样高的神童,不学习,最终也变成了普通人一样。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然的话,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办不到。
赏析二:文章开头一段,记叙了方仲永幼年聪颖的情况。先点出其“世隶耕”,出身世代为农的家庭,为下面写他的天资作铺垫。
接着,写他五岁时忽然无师自通、书诗署名的突出表现。这几句写得颇具神奇色彩。
本来“未尝识书具”——农家无笔墨纸砚,却“忽啼求之”;求得之后,不但“即书诗四句”,且“自为其名”;从此以后,又竟“指物作诗立就”。这自然被乡人视为神童了。
因为“奇”其子,连带着“稍稍宾客其父”,甚至给他钱。这本来是山乡百姓对有天资的儿童及其家庭的敬重,但竟反过来成了压抑天资的不利条件。
“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儿童的天资被无知的父亲利用来作为到处敛钱的资本,亟需在求学中发展的天资竟“不使学”。
作者对这种因没有文化和贫困带来的愚昧,在叙述中寓有讽慨;而对被利用来到处讨钱的仲永,则不无“伤”意。这几句是本段中的关键之笔。
仲永后来的结局与作者的议论,都由此伏根。“不使学”三字用笔尤重。
整段叙述,从“未尝识书具”到“指物作诗立就”到“不使学”,文意曲折多变,使读者对仲永的将来发展引起极大的兴趣。 接下来一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代了仲永从神通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
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之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代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
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
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现言外。 最后一段(教材中被省略,建议作为补充阅读材料)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