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黄山记文言文翻译(《游黄山记》文言文翻译)
1.《游黄山记》文言文翻译
山用黄来命名,记述陈旧的遗迹。以往春申君黄歇曾经在这个地方读书,因此而得名。那山下有一片竹林,特产方竹。往北是是渔庄,三尺板桥,一湾流水,竹林小径,点点茅屋,像鱼鳞木梳一样整齐密密而又整齐地排列。春季第二个月,清新趣味满眼,惹人宠爱的燕子啄着鲜花,娇小的黄莺坐在柳树上嬉戏,仿佛是在画图中一样。登上高山向东望去,大江和远天相接,沙鸟和风帆,时隐时现的。深冬下雪,云气悠远,大雪履盖着江边,千里只有白茫茫一片。一年之内,景致各不相同。于是访求农夫,拜渔夫,想访求春申君的旧址,而一些老农尚且有不知道春申君是什么人。
唉!这正是老农们的幸运,也是春申君的不幸。春申君离世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这些老农正处于太平盛世,生活在无战事的年代,耕田打井自求安乐,饱食过后嬉戏游玩,这实在是所说不了解不知晓纷乱的人,又有谁还会计较千百年以上还有一个所说的春申君这个人呢?
我替父老们感到幸运,我替春申君感到悲哀,于是创作黄山之歌说:“您还没有出生时,山已经存在了。您于世长辞了,山还依旧长存。谁是终结谁是开始,是您呢还是山呢?” 又创作到:“君靠山,欣喜有所寄托。山靠您,因而成就名声。谁更显达谁更隐晦,是山呢还是您呢?

2.徐宏祖<游黄山记>的译文是什么?
游黄山日记(后)〔明〕徐弘祖戊午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
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 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
扶杖望朱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
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
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
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
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
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勇。
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
余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
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
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
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
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
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
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一坞幽然。
别澄源,下山至前岐路侧,向莲花峰而趋。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将下百步云梯,有路可直跻莲花峰。
既陟而磴绝,疑而复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莲花道也!”乃从石坡侧度石隙,径小而峻,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
从其中叠级直上,级穷洞转,屈曲奇诡,如下上楼阁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庐,倚石罅中。
方徘徊欲升,则前呼道之僧至矣。僧号凌虚,结茅于此者,遂与把臂陟顶。
顶上一石,悬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巅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
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庵,凌虚出粥相饷,啜一盂。
乃下至岐路侧,过大悲顶,上天门。三里,至炼丹台。
循台嘴而下,观玉屏风、三海门诸峰,悉从深坞中壁立起。其丹台一冈中垂,颇无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坞中峰峦错耸,上下周映,非此不尽瞻眺之奇耳。
还过平天矼,下后海,入智空庵,别焉。三里,下狮子林,趋石笋矼,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
瞰坞中峰石回攒,藻缋满眼,始觉匡庐、石门,或具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闳博富丽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坞中,阴阴觉有异。复至冈上尖峰侧,践流石,援棘草,随坑而下,愈下愈深,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尽也。
日暮,返狮子林。初六日别霞光,从山坑向丞相原下。
七里,至白沙岭。霞光复至,因余欲观牌楼石,恐白沙庵无指者,追来为导。
遂同上岭,指岭右隔坡,有石丛立,下分上并,即牌楼石也。余欲逾坑溯涧,直造而下。
僧谓:“棘迷路绝,必不能行,若此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复上此岭;若欲从仙灯而往,不若即由此岭东向。”余从之,循岭脊行。
岭横亘天都、莲花之北,狭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夹映。岭尽北下,仰瞻右峰罗汉石,圆头秃顶,俨然二僧也。
下至坑中,逾涧而上,共四里,登仙灯洞。洞南向,正对天都之阴。
僧架阁连板于外,而内犹穹然,天趣未尽刊也。复南下三里,过丞相原,山间一夹地耳。
其庵颇整,四顾无奇,竟不入。复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渐下,涧中泉声沸然,从石间九级下泻,每级一下有潭渊碧,所谓九龙潭也。
黄山无悬流飞瀑,惟此耳。又下五里,过苦竹滩,转循太平县路,向东北行。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徐霞客游记》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初三 我们一行离开白岳山榔梅庵,到了桃源桥,从小桥右面而下,山路异常陡峭,这就是上次游黄山时所走的路。往前走七十里,夜宿在江村。
初四日 步行十五里路到达汤口。再五里,来到汤寺,在汤池洗了澡,便拄着手杖朝朱砂庵方向攀登。
走了十里路,登上黄泥冈,原先被云雾遮没的诸山峰,渐渐显露出来,又渐渐落到了我的手杖底下。转入石门,经天都峰半山腰而下,则天都、莲花两座峰顶,都以秀美的英姿兀立在半空。
路旁有一岔道朝东而上,却是昔日所未到之处,于是往前直上,差不多到达天都峰旁。再往北而上,攀行在石隙之中。
只见两侧峰石一片片夹峙而起,山道迂回曲折于岩石间,遇到山石阻塞就凿通它,遇到山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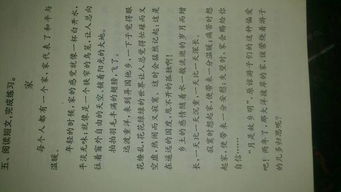
3.<<游黄山记 袁枚>>文言 翻译
原文: 初四日。
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
扶杖望朱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
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
路旁一歧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
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坡,灿若图绣。
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 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
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勇。
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
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莲花可登而路遥。祗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
余不从,决意游天都。 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
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
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
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
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
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于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钜,雾气去来无定。
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
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止文殊院。
译文: 九月初四这天。(动身行走)十五里到汤口。
(又走)五里到汤寺,在汤池洗了澡。拄着拐杖望着朱砂庵攀登。
(走了)十里,上到黄泥冈。(这时)先前云雾笼罩着的那些山峰,渐渐地露出来了,也渐渐地落到我的手杖底下。
转身进入石门峰,经过天都峰的山腰下来,就(望见)天都、莲花两峰顶,都高高地耸出半天之外。路旁有一条岔路向东直上,是前次(游山时)没有到过的,于是向前直往上走,差不多到了天都峰侧面了。
再往北上,走在狭谷中的小道上。石峰一片片地夹立高耸;路就在石峰间宛转延伸,石头堵塞的地方就把它凿开,陡峭的地方把它凿成石级,中断的地方就架上木头,使它畅通,高悬的地方就树起梯子连接。
向下看,(只见)陡峻的山谷气象阴森,枫树、松树杂然相间,五色缤纷,灿烂得象图画,象锦绣。因此想到黄山算得是我生平所看到的奇景,而有这样的奇景,前次游山却未来探访,这次游山真是既痛快而又惭愧呀! 这时仆人们都因路险阴隔,落在后面,我也停下来不向上攀登;可是一路上奇丽的景色,不觉又吸引着我一人走上去了。
已经登上山头,见一个小寺庙,檐角翘起,象小鸟张开翅膀似的立在那儿,这就是文殊院,也是我从前想登而没有登的地方。(它)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背后倚的是玉屏风,两峰秀丽的景色,(好象)都可以伸手揽取。
四周环顾,奇峰错落地排列,众多的山谷纵横交错,实在是黄山风景最美的地方!如果不是重来,怎么知道它如此奇丽呢?遇见云游的和尚澄源来了,(我们)游兴很浓。时间已过正午,仆人们也刚刚赶到。
(我们)站在寺庙前面,(望着)两峰指指点点。庵中和尚说:“天都峰虽近,可是无路可通,莲花峰可登,路却又太远。
(看来)只好就近处望望天都峰,明天再登莲花峰顶吧”。我不同意,决意游天都峰。
(便)带着澄源和仆人仍从峡谷小路下来。到天都峰侧,从那被山溪冲下来的乱石上象蛇一样弯弯曲曲地爬上去。
攀杂草,牵荆棘,石块丛起的地方就越过石块,石崖侧削的地方就攀缘石壁。每到手脚没有着落的地方,澄源总是先攀上去,再俯身接应(我)。
常常想到上山既然这样困难,下山更不知怎么办了?最后还是不管那些。经过多次艰险,终于到达峰顶。
只是它上面还有一座石峰,象一堵墙壁耸起好象有几十丈高,澄源在它的旁边寻找,发现有石级,就拉着我登上去。(到那一看)万千峰峦,无不躬身下伏,只有莲花峰能和它抗衡罢了。
这时浓雾忽起忽散,每来一阵,就对面不见人。远望莲花诸峰,多半隐在雾中。
独自登上天都峰,我走到前面,雾就飘到我后面去了;我走到右边,雾就从左边出来了。那些松树还有盘曲挺拨纵横交错的;柏树虽然大枝干粗如手臂,(可是)都平贴在石上,好象苔藓似的。
山高风大,雾气来去不定。下望群峰,有时露出来象碧绿的山尖,有时被雾淹没了象一片银海;再远眺山下,日光晶莹闪亮,别有一番天地啊。
天色渐晚,于是就把双脚伸向前边,手向后按着地面,坐着往下滑;到极危险的地方,澄源肩手并用,把我接下去。过了险处,下到山坳,已经夜色笼罩了。
又从峡谷中经过栈道上山,(回到)文殊院留宿。
4.徐霞客的<游黄山记>的翻译 是什么啊
戊午年(公元1618年)九月初三,我从白岳榔梅庵出发,到了桃源桥。
从小桥右边下山,山坡非常陡,这就是从前通向黄山的路。走了七十里地,投宿在江边的一个村庄。
初四,走了十五里路,到了汤口。又走了五里,到了汤寺,在汤池里边沐浴。
拄着拐杖向着朱砂庵攀登。走了十里,上到了黄泥冈。
这时云雾里边的各个山峰,渐渐露出来,又渐渐的落到我的拐杖底下。拐进石门,越过陡峭的天都峰的威胁往下看,天都峰、莲花峰两座山峰,都有一半插入云霄,选一条路的分支往东攀登,那是从前我没有到过的地方,于是一直往上爬,几乎到达了天都峰的山坡。
又往北上,在石缝里攀行。山峰相对耸立,中间只有一条缝;山路在石头之间蜿蜒不断,又堵塞的地方就凿开它,陡峭的地方就凿出台阶,断裂的地方就用木头搭桥连通它们,高悬的地方就用梯子搭上。
往下俯视,陡峭的山谷非常阴森,枫树和松树交错混杂,五色缤纷,灿烂的好像画出来或绣出来的。因此感觉黄山是我一生见到的奇观,但是奇妙到这种地步,从前没有来过,这次游历真是又痛快又惭愧啊! 这是我的从人都害怕险阻停下了,我也停下没有继续上去;但是一路奇景,不觉的引诱我独自前往。
登上峰顶以后,有一座庙庵像翅膀一样伸出来,这是文殊院,也是我当年打算登上却没有登上的地方。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后边倚着玉屏风峰,两座山峰的秀丽景色,用手就能揽过来。
向四周看奇峰交错耸立,许多山谷纵横交错,真是黄山的绝美的地方!如果不是再来一次(前度已来过一次),怎么能知道这里如此奇妙?碰到了云游的和尚(法号澄源),非常兴奋。过了中午,我的从人恰好到了。
站在文殊院前,指点着两座山峰。院里的和尚说:“天都峰虽然近但是没有路,莲花峰可以登上但是路远。
今天只适合靠近天都峰而观赏,明日再登上莲花峰峰顶。”我不同意,决心去攀天都峰。
带着澄源和尚、下人又走下窄路。到达天都峰旁边,从流石曲折而上。
抓着草和荆棘,遇到石块就越过石块,遇到石崖就攀登石崖。每当到了手脚都没有地方放的地步,澄源和尚一定率先登上然后再垂头拉我们。
一想到往上爬尚且如此,往下走如何得了?最后就顾不上想这么多了。多次遇到险情,中遇到到了峰顶。
只有一块石头在山顶几十丈大,澄源和尚在旁边寻路,找到一个台阶,扶着我往上爬。所有的山峰都好像往下走,只有莲花峰和它相当。
这时浓雾一会起一会停,第一阵刚起来,就看不到对面的人。眺望莲花峰,大多都在雾里。
我独自爬天都峰,予到了前头,则雾就跑到后头;我到了右边,则雾跑到左边。这里的松树依然有弯曲、挺拔交错的;柏树虽然比手臂粗,都平贴在石头上、就像苔藓的样子。
山高风大,雾气来来去去也不定。往下看各山峰,一会出现绿色尖而高的山,一会隐没成银色的海洋。
再往山下看,日光闪耀,真是另一种景象。快到了傍晚,于是脚放在前边,手在后边扶着地,坐着往下走。
到了绝险的地方,澄源和尚就用手照应着我。过了仙境,到了山沟,天色很晚了。
又从那条窄路往上走,到了文殊院。 初五,天一亮,我们从天都峰的山沟中往北走下二里路,石壁耸然而立。
下面的莲花洞正好和前面石坑里的石笋对峙,一做山坞幽然坐落在那里。告别了澄源和尚,下山到了分叉的路的旁边,向莲花峰前进。
一路顺着陡峭的崖壁往西走,又向下再往上,刚要走下一百步长的云梯,发现有条路可仪直接通向莲花峰。但是路很陡几乎上不去,郑怀疑要往下走。
对面山峰的一个和尚高声喊:“这正是去莲花峰的路!”于是从石玻的侧面越过大石缝。路很窄而且陡峭,峰顶都是巨石耸立,中间空空的就像屋子。
从其中的台阶径直往上,台阶尽头转进山洞,曲折诡秘,就像空中的楼阁,忘记了这是险峻的靠近天的地方。走了一里见到一座茅庐,坐落在石缝中。
正犹豫是否开门,刚才呼喊的那个和尚到了,他法号凌虚,就是在这里建造茅庐的人,于是和他共同爬山顶。顶上有一块石头,有二丈高,和尚找出梯子来向上爬。
山顶豁然开阔,向四周眺望天空,天都峰也在下边了。大盖这座山峰坐落在黄山的中央,只有它比别的山峰高,四面岩壁耸立,遇到朝阳的照射放出晴朗的色彩,层层亮光,让人狂叫,想要跳舞。
过了很长时间,回到了茅庐,凌虚和尚熬粥款待我,我喝了一佛盂,于是下山。到了分叉的路的旁边,经过大悲顶,爬上天门。
过了三里地,到了炼丹台。沿着台嘴往下走,观看玉屏风、三海门等各山峰,都从深邃的山坞中耸立而出。
炼丹台有一个山冈下垂,没什么险峻的其实,只有俯视翠微峰的背面,山坞中峰峦交错,上下辉映,不看这里就体会不全眺望的奇异景色。回来的时候经过平天矼,走下后海,到了智空庵,有告别庵里的和尚。
走了三里,经过狮子林,走向石笋矼,到了去年登上的峰顶上。倚着松树坐下,俯视山坞里峰、石错杂,满眼都是如画的景色,才发现匡庐、石门,有的好像一个整体,有的缺少一面,不像这里宽广宏大丰富富丽!过了很长时间,向上攀登山崖,向下眺望山坞,隐隐觉得不对劲。
又走回山冈上尖峰的旁边,踩着流石,抓着棘草,沿着石坑往下,越下越。
5.求袁枚《游黄山记》全文翻译
原文 癸卯四月二日,余游白岳毕,遂浴黄山之汤泉、泉甘且冽,在悬崖之下。
夕宿慈光寺。 次早,僧告曰:“从此山径仄险,虽兜笼①不能容。
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惯负客者,号海马,可用也。”引五六壮佼者来,俱手数丈布。
余自笑羸老乃复作襁褓儿耶?初犹自强,至惫甚,乃缚跨其背。于是且步且负各半。
行至云巢,路绝矣,蹑木梯而上,万峰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
天雨寒甚,端午犹披重裘拥火。云走入夺舍,顷刻混沌,两人坐,辨声而已。
散后,步至立雪台,有古松根生于东,身仆于西,头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与之相化。
又似畏天,不敢上长,大十围,高无二尺也。他松类是者多,不可胜记。
晚,云气更清,诸峰如儿孙俯伏。 次日,从台左折而下,过百步云梯,路又绝矣。
忽见一石如大鳌鱼,张其口。不得已走入鱼口中,穿腹出背,别是一天。
登丹台,上光明顶,与莲花、天都二峰为三鼎足,高相峙。天风撼人,不可立。
晚至狮林寺宿矣。趁日未落,登始信峰。
峰有三,远望两峰尖峙,逼视之,尚有一峰隐身落后。峰高且险,下临无底之溪,余立其巅,垂趾二分在外。
僧惧挽之。余笑谓:“坠亦无妨。”
问:“何也?”曰:“溪无底,则人坠当亦无底,飘飘然知泊何所?纵有底,亦须许久方到,尽可须臾求活。”僧人笑。
次日,登大小清凉台。台下峰如笔,如矢,如笋,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戏将武库兵仗布散地上。
食顷,有白练绕树。僧喜告曰:“此云铺海也。”
初蒙蒙然,镕银散绵,良久浑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类大盘凝脂中有笋脯矗现状。
俄而离散,则万峰簇簇,仍还原形。余坐松顶苦日炙,忽有片云起为荫遮,方知云有高下,迥非一族。
译文 癸卯四月二日,我游览了白岳峰后,就在沐浴了黄山的温泉。泉水甜美而清冽,在悬崖的下面。
晚上在慈光寺住宿。 第二天早上,和尚告诉我说:“从这里开始,山路狭窄危险,连兜笼也容不下。
你自己步行太辛苦,幸亏当地有背惯了游客的人,叫做‘海马’,可以雇佣。”便领了五六个健壮的人来,人人手里拿着几丈布。
我自觉好笑,难道瘦弱的老人又重新做了襁褓中的婴儿了吗?开始时还想强撑着自己走,等到疲劳不堪时,就绑缚在“海马”的背上,这样一半自己走一半靠人背着攀登。走到云巢路断了,只有踩着木梯子上去。
只见万座山峰直刺苍穹,慈光寺已经落在锅底了。当晚到达文殊院,住了下来。
天下着雨,非常冷,正午还要穿着厚皮衣烤火取暖。云气直扑进屋,像要把房子夺去,一会儿功夫,屋内一片云雾迷蒙,两人对面坐着仅能听到声音,云气散后,步行到立雪台,台上有棵古松,根生长在东面,树干倒向西面,树冠朝着南方,穿进山石中,又穿裂山石生长出来,山石像是活的,似乎中间是空的,所以树干能藏身其中,而和山石合为一体。
又像是害怕天公而不敢向上生长,树干有十围粗,高度却不到二尺。其他松树像这样的很多,无法一一加以描述。
晚上,云气更加稀薄,周围的山峰像儿孙拜见长辈一样俯伏着。 第二天,从立雪台左侧转弯走下来,经过百步云梯,路又断了,忽然见一块石头像大鳌鱼,张着巨口,不得已只好走进鱼口中,穿过鱼腹从鱼背上出来,看到的又是一番天地。
登上丹台,爬上光明顶,它和莲花、天都两座山峰,像鼎的三条腿一样高高地相互对峙,天风吹得人站立不住。晚上到达狮林寺住宿。
趁太阳未落,又登上始信峰。始信峰有三座山峰,远看好像只有两座山峰相对耸立,近前看才见另一座山峰躲在它们身后。
始信峰既高又险,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溪谷。我站在山顶,脚趾都露出二分在悬崖外边。
和尚担心,用手拉住我。我笑着说:“掉下去也不要紧。”
和尚问道:“为什么?”我说:“溪谷没有底,那么人掉下去也就没有底,飘飘荡荡谁知道飘到哪里去?即使有底,也要很久才能到,完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找到活的办法。”和尚笑了起来。
第二天,攀登大小清凉台,台下的峰峦像笔,像箭,像笋,像竹林,像刀枪剑戟,像船上的桅杆,又像天帝开玩笑把武器库中的武器仪仗全散落在地上,大约有吃一顿饭的功夫, 像有一匹白绢飘过来缠绕着树木,僧人高兴告诉我说:“这就是云铺海。”开始时朦朦胧胧,像熔化的白银,散开的棉团,过了很久浑然成了一片。
青山全都露出一点角尖,像一大盘白油脂中有很多笋尖竖立的样子,一会儿云气散去,只见万座山峰聚集耸立,又都恢复了原貌。我坐在松顶,苦于太阳晒得厉害,忽然起了一片云彩为我遮蔽,才知道云彩也有高下的区别,不全是一模一样的。
初九日,从天柱峰转道下来,过白沙矼,到达云谷,家里的佣人们用轿子迎接我,这次共计步行五十多里路,进山一共七天。 呵呵,不在的是不是的.。
6.袁枚<<游黄山记>>全文翻译
译文
癸卯四月二日,我游览了白岳峰后,就在沐浴了黄山的温泉。泉水甜美而清冽,在悬崖的下面。晚上在慈光寺住宿。
第二天早上,和尚告诉我说:“从这里开始,山路狭窄危险,连兜笼也容不下。你自己步行太辛苦,幸亏当地有背惯了游客的人,叫做‘海马’,可以雇佣。”便领了五六个健壮的人来,人人手里拿着几丈布。我自觉好笑,难道瘦弱的老人又重新做了襁褓中的婴儿了吗?开始时还想强撑着自己走,等到疲劳不堪时,就绑缚在“海马”的背上,这样一半自己走一半靠人背着攀登。走到云巢路断了,只有踩着木梯子上去。只见万座山峰直刺苍穹,慈光寺已经落在锅底了。当晚到达文殊院,住了下来。
天下着雨,非常冷,正午还要穿着厚皮衣烤火取暖。云气直扑进屋,像要把房子夺去,一会儿功夫,屋内一片云雾迷蒙,两人对面坐着仅能听到声音,云气散后,步行到立雪台,台上有棵古松,根生长在东面,树干倒向西面,树冠朝着南方,穿进山石中,又穿裂山石生长出来,山石像是活的,似乎中间是空的,所以树干能藏身其中,而和山石合为一体。又像是害怕天公而不敢向上生长,树干有十围粗,高度却不到二尺。其他松树像这样的很多,无法一一加以描述。晚上,云气更加稀薄,周围的山峰像儿孙拜见长辈一样俯伏着。
第二天,从立雪台左侧转弯走下来,经过百步云梯,路又断了,忽然见一块石头像大鳌鱼,张着巨口,不得已只好走进鱼口中,穿过鱼腹从鱼背上出来,看到的又是一番天地。登上丹台,爬上光明顶,它和莲花、天都两座山峰,像鼎的三条腿一样高高地相互对峙,天风吹得人站立不住。晚上到达狮林寺住宿。趁太阳未落,又登上始信峰。始信峰有三座山峰,远看好像只有两座山峰相对耸立,近前看才见另一座山峰躲在它们身后。始信峰既高又险,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溪谷。我站在山顶,脚趾都露出二分在悬崖外边。和尚担心,用手拉住我。我笑着说:“掉下去也不要紧。”和尚问道:“为什么?”我说:“溪谷没有底,那么人掉下去也就没有底,飘飘荡荡谁知道飘到哪里去?即使有底,也要很久才能到,完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找到活的办法。”和尚笑了起来。
第二天,攀登大小清凉台,台下的峰峦像笔,像箭,像笋,像竹林,像刀枪剑戟,像船上的桅杆,又像天帝开玩笑把武器库中的武器仪仗全散落在地上,大约有吃一顿饭的功夫,
像有一匹白绢飘过来缠绕着树木,僧人高兴告诉我说:“这就是云铺海。”开始时朦朦胧胧,像熔化的白银,散开的棉团,过了很久浑然成了一片。青山全都露出一点角尖,像一大盘白油脂中有很多笋尖竖立的样子,一会儿云气散去,只见万座山峰聚集耸立,又都恢复了原貌。我坐在松顶,苦于太阳晒得厉害,忽然起了一片云彩为我遮蔽,才知道云彩也有高下的区别,不全是一模一样的。
初九日,从天柱峰转道下来,过白沙矼,到达云谷,家里的佣人们用轿子迎接我,这次共计步行五十多里路,进山一共七天。
7.谁有徐宏祖<游黄山记>的译文
游黄山日记(后)〔明〕徐弘祖戊午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
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 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
扶杖望朱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
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
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
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
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
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勇。
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
余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
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
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
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
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
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
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一坞幽然。
别澄源,下山至前岐路侧,向莲花峰而趋。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将下百步云梯,有路可直跻莲花峰。
既陟而磴绝,疑而复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莲花道也!”乃从石坡侧度石隙,径小而峻,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
从其中叠级直上,级穷洞转,屈曲奇诡,如下上楼阁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庐,倚石罅中。
方徘徊欲升,则前呼道之僧至矣。僧号凌虚,结茅于此者,遂与把臂陟顶。
顶上一石,悬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巅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
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庵,凌虚出粥相饷,啜一盂。
乃下至岐路侧,过大悲顶,上天门。三里,至炼丹台。
循台嘴而下,观玉屏风、三海门诸峰,悉从深坞中壁立起。其丹台一冈中垂,颇无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坞中峰峦错耸,上下周映,非此不尽瞻眺之奇耳。
还过平天矼,下后海,入智空庵,别焉。三里,下狮子林,趋石笋矼,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
瞰坞中峰石回攒,藻缋满眼,始觉匡庐、石门,或具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闳博富丽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坞中,阴阴觉有异。复至冈上尖峰侧,践流石,援棘草,随坑而下,愈下愈深,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尽也。
日暮,返狮子林。初六日别霞光,从山坑向丞相原下。
七里,至白沙岭。霞光复至,因余欲观牌楼石,恐白沙庵无指者,追来为导。
遂同上岭,指岭右隔坡,有石丛立,下分上并,即牌楼石也。余欲逾坑溯涧,直造而下。
僧谓:“棘迷路绝,必不能行,若此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复上此岭;若欲从仙灯而往,不若即由此岭东向。”余从之,循岭脊行。
岭横亘天都、莲花之北,狭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夹映。岭尽北下,仰瞻右峰罗汉石,圆头秃顶,俨然二僧也。
下至坑中,逾涧而上,共四里,登仙灯洞。洞南向,正对天都之阴。
僧架阁连板于外,而内犹穹然,天趣未尽刊也。复南下三里,过丞相原,山间一夹地耳。
其庵颇整,四顾无奇,竟不入。复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渐下,涧中泉声沸然,从石间九级下泻,每级一下有潭渊碧,所谓九龙潭也。
黄山无悬流飞瀑,惟此耳。又下五里,过苦竹滩,转循太平县路,向东北行。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徐霞客游记》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初三 我们一行离开白岳山榔梅庵,到了桃源桥,从小桥右面而下,山路异常陡峭,这就是上次游黄山时所走的路。往前走七十里,夜宿在江村。
初四日 步行十五里路到达汤口。再五里,来到汤寺,在汤池洗了澡,便拄着手杖朝朱砂庵方向攀登。
走了十里路,登上黄泥冈,原先被云雾遮没的诸山峰,渐渐显露出来,又渐渐落到了我的手杖底下。转入石门,经天都峰半山腰而下,则天都、莲花两座峰顶,都以秀美的英姿兀立在半空。
路旁有一岔道朝东而上,却是昔日所未到之处,于是往前直上,差不多到达天都峰旁。再往北而上,攀行在石隙之中。
只见两侧峰石一片片夹峙而起,山道迂回曲折于岩石间,遇到山石阻塞就凿通它,遇到山崖。
8.求袁枚《游黄山记》全文翻译
原文 癸卯四月二日,余游白岳毕,遂浴黄山之汤泉、泉甘且冽,在悬崖之下。
夕宿慈光寺。 次早,僧告曰:“从此山径仄险,虽兜笼①不能容。
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惯负客者,号海马,可用也。”引五六壮佼者来,俱手数丈布。
余自笑羸老乃复作襁褓儿耶?初犹自强,至惫甚,乃缚跨其背。于是且步且负各半。
行至云巢,路绝矣,蹑木梯而上,万峰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
天雨寒甚,端午犹披重裘拥火。云走入夺舍,顷刻混沌,两人坐,辨声而已。
散后,步至立雪台,有古松根生于东,身仆于西,头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与之相化。
又似畏天,不敢上长,大十围,高无二尺也。他松类是者多,不可胜记。
晚,云气更清,诸峰如儿孙俯伏。 次日,从台左折而下,过百步云梯,路又绝矣。
忽见一石如大鳌鱼,张其口。不得已走入鱼口中,穿腹出背,别是一天。
登丹台,上光明顶,与莲花、天都二峰为三鼎足,高相峙。天风撼人,不可立。
晚至狮林寺宿矣。趁日未落,登始信峰。
峰有三,远望两峰尖峙,逼视之,尚有一峰隐身落后。峰高且险,下临无底之溪,余立其巅,垂趾二分在外。
僧惧挽之。余笑谓:“坠亦无妨。”
问:“何也?”曰:“溪无底,则人坠当亦无底,飘飘然知泊何所?纵有底,亦须许久方到,尽可须臾求活。”僧人笑。
次日,登大小清凉台。台下峰如笔,如矢,如笋,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戏将武库兵仗布散地上。
食顷,有白练绕树。僧喜告曰:“此云铺海也。”
初蒙蒙然,镕银散绵,良久浑成一片。青山群露角尖,类大盘凝脂中有笋脯矗现状。
俄而离散,则万峰簇簇,仍还原形。余坐松顶苦日炙,忽有片云起为荫遮,方知云有高下,迥非一族。
译文 癸卯四月二日,我游览了白岳峰后,就在沐浴了黄山的温泉。泉水甜美而清冽,在悬崖的下面。
晚上在慈光寺住宿。 第二天早上,和尚告诉我说:“从这里开始,山路狭窄危险,连兜笼也容不下。
你自己步行太辛苦,幸亏当地有背惯了游客的人,叫做‘海马’,可以雇佣。”便领了五六个健壮的人来,人人手里拿着几丈布。
我自觉好笑,难道瘦弱的老人又重新做了襁褓中的婴儿了吗?开始时还想强撑着自己走,等到疲劳不堪时,就绑缚在“海马”的背上,这样一半自己走一半靠人背着攀登。走到云巢路断了,只有踩着木梯子上去。
只见万座山峰直刺苍穹,慈光寺已经落在锅底了。当晚到达文殊院,住了下来。
天下着雨,非常冷,正午还要穿着厚皮衣烤火取暖。云气直扑进屋,像要把房子夺去,一会儿功夫,屋内一片云雾迷蒙,两人对面坐着仅能听到声音,云气散后,步行到立雪台,台上有棵古松,根生长在东面,树干倒向西面,树冠朝着南方,穿进山石中,又穿裂山石生长出来,山石像是活的,似乎中间是空的,所以树干能藏身其中,而和山石合为一体。
又像是害怕天公而不敢向上生长,树干有十围粗,高度却不到二尺。其他松树像这样的很多,无法一一加以描述。
晚上,云气更加稀薄,周围的山峰像儿孙拜见长辈一样俯伏着。 第二天,从立雪台左侧转弯走下来,经过百步云梯,路又断了,忽然见一块石头像大鳌鱼,张着巨口,不得已只好走进鱼口中,穿过鱼腹从鱼背上出来,看到的又是一番天地。
登上丹台,爬上光明顶,它和莲花、天都两座山峰,像鼎的三条腿一样高高地相互对峙,天风吹得人站立不住。晚上到达狮林寺住宿。
趁太阳未落,又登上始信峰。始信峰有三座山峰,远看好像只有两座山峰相对耸立,近前看才见另一座山峰躲在它们身后。
始信峰既高又险,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溪谷。我站在山顶,脚趾都露出二分在悬崖外边。
和尚担心,用手拉住我。我笑着说:“掉下去也不要紧。”
和尚问道:“为什么?”我说:“溪谷没有底,那么人掉下去也就没有底,飘飘荡荡谁知道飘到哪里去?即使有底,也要很久才能到,完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找到活的办法。”和尚笑了起来。
第二天,攀登大小清凉台,台下的峰峦像笔,像箭,像笋,像竹林,像刀枪剑戟,像船上的桅杆,又像天帝开玩笑把武器库中的武器仪仗全散落在地上,大约有吃一顿饭的功夫, 像有一匹白绢飘过来缠绕着树木,僧人高兴告诉我说:“这就是云铺海。”开始时朦朦胧胧,像熔化的白银,散开的棉团,过了很久浑然成了一片。
青山全都露出一点角尖,像一大盘白油脂中有很多笋尖竖立的样子,一会儿云气散去,只见万座山峰聚集耸立,又都恢复了原貌。我坐在松顶,苦于太阳晒得厉害,忽然起了一片云彩为我遮蔽,才知道云彩也有高下的区别,不全是一模一样的。
初九日,从天柱峰转道下来,过白沙矼,到达云谷,家里的佣人们用轿子迎接我,这次共计步行五十多里路,进山一共七天。 呵呵,不在的是不是的.。
9.袁枚的 《游黄山记》译文
只有原文。
次日,从台左折而下,过百步云梯,路又绝矣。忽见一石,如大鳌鱼,张其口。
不得已,走入鱼口中,穿腹,出背,别是一天。登丹台,上光明顶,与莲花、天都二峰为三,鼎足高相峙;天风撼人不可立,幸松针铺地二尺厚,甚软,可坐。
晚至狮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峰。
峰有三,远望两峰夹峙,逼视之,尚有一峰隐身落后。峰高且险,下临无底之溪。
余立其巅,垂趾二分在外,僧惧,挽之。余笑谓:“坠亦无妨。”
问:“何也?”曰:“溪无底,则人坠当亦无底,飘飘然知泊何所?纵有底,亦须许久方到,尽可须臾求活。惜未挈长绳,缒精铁量之,果若干尺耳。”
僧大笑。


